本文轉自公眾號 將門創投,原文地址
當卡爾 · 本茨發明汽車,人類進入汽車時代時,科學技術就對人類的 “ 出行 ” 進行了新的定義,而隨着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進步, 人類對於智能駕駛這一夢想有了新的期待與希冀。那麼,智能駕駛是如何起源、孕育、發展、爆發的呢?從中我們能夠獲得什麼樣的啟發?本文將回顧這一歷史,並探討新興戰略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途徑。
信息技術發展具有20年的周期律:1970年至1990年是發軔於PC的數字化,1990年至2010年是互聯網推動的網絡化,而從2010年開始的這20年,我們面臨的將是人工智能的寒武紀大爆發。
目前,人工智能炙手可熱,創業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業者開始思考,如何讓技術形成漣漪效應,促使產業非線性、躍遷式增長。
有人把人工智能和產業的關係比喻成 “ 葡萄乾和麵包 ” ,雖然葡萄乾離開麵包仍是葡萄乾,但兩者結合在一起就能創造出高價值的新品類。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的產業機會,並得出結論:未來15年,智能駕駛將是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增值最大的產業,沒有之一。
首先,激活、重塑和創造多個 萬億級 市場。
- 激活汽車市場,智能、安全和人機共駕的新體驗將重新激起人們換車的需求;
- 重塑出行市場,無人駕駛 + 共享汽車將解決如今困擾消費者和出行服務商的最大問題——司機成本和 “ 壞人 ” 風險。如果說當前的網約車只解決了 2 % 的出行,那麼未來無人駕駛出租車可以將這個比例提升數十倍;
- 創造了新的消費經濟和生產力市場——乘客經濟。乘客在路上或消費,或工作,或娛樂,每一輛車都可以變成移動的商業地產。
其次,解決人類進入汽車社會以來一直無法解決的多個社會問題 ——交通擁堵(以及怠速行駛帶來的廢氣排放)、事故頻發、停車難等。無人駕駛如同具有千億公里的駕駛經驗和百萬年駕齡的“ 老司機”,不疲勞、不路怒、不酒駕葯駕、不隨意加塞、也不用操心停車,可以根本性解決上述問題,真正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智能駕駛的發展,可以分成 4 個階段:
2004 年以前;
2004 年 – 2009年:第一個 6 年——孕育;
2010 年 – 2015 年:第二個 6 年——成長;
2016 年 – 2021 年:第三個 6 年——開花;
2022 年 – 2027 年:第四個 6 年——結果。
2004 年以前——自動駕駛的前世
1921 年 8 月,第一輛無人駕駛(實為遙控)汽車在美國誕生,美國陸軍的一位電子工程師坐在後面的一輛車上,用無線電操控前面那輛無人車的方向盤、離合器和制動器。
1939 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通用汽車在 “ 未來世界 ” 展覽上,預言 1960 年高速公路將具有電子軌道,與汽車的自動駕駛系統相配合,實現無人駕駛,直到駛出高速公路才切換回司機駕駛。
此後,通用汽車並沒有把這個預言當做兒戲,而是在 1956 年展出了 Firebird II,這輛看似 “火箭” 的概念車有史以來第一次具備了自動導航系統。兩年以後,Firebird III 問世時,BBC 現場直播了基於車路協同的無人駕駛,高速公路上預埋的線纜與車端的接收器通過電子脈衝信號進行通訊,展示了未來高速公路的無人駕駛形態。
實際上,真正具備獨立自動駕駛能力的原型——Shakey,出現在 20 世紀 60 年代,誕生於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這個研究院後來改名為斯坦福國際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以發明了電腦鼠標和語音助手 Siri 聞名,它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機器人。
Shakey 是第一個具有完整感知、規劃和控制能力(這也是後來機器人和無人車的通用框架)的機器人。Shakey 之父是科學怪才查爾斯·羅森(Charles Rosen),也是斯坦福國際研究院的創始人。獵奇的媒體對 Shakey 做出了超出其實際能力,甚至聳人聽聞的宣傳,末日論第一次泛起,這讓科學家們頗為尷尬,而這也是人工智能學界第一次與媒體結下了梁子,後來無數次反覆。
如果說 Shakey 只是個在室內移動的機器人,那麼 “斯坦福車(Stanford Cart)” 則是第一輛接近於無人駕駛汽車的機器人。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被譽為“人工智能最堅定的支持者”,在他的領導下,“斯坦福車”取得了巨大進展。莫拉維克的團隊研發了很多新技術,例如,用單一攝像頭計算場景的深度,後來 Mobileye 採用了類似技術。多數情況下,“斯坦福車” 需要通過遠程圖像來操控,有一次它逃脫了控制,直接駛入了繁忙的道路,當莫拉維克從監視器中看到一輛真實的車輛從 “斯坦福車” 邊上呼嘯而過,大吃一驚,於是追捕“叛逃機器人”成為無人車歷史上詼諧的一筆。
莫拉維克在機器視覺的探索中遭遇了很多挫折,後來提出了著名的莫拉維克悖論(Moravec’s Paradox)——人類的高階智能,比如推理、規劃和下棋,計算機都能夠輕易實現。而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就能駕輕就熟的低階智能,如感知和運動配合,計算機都遙不可及。在深度學習尚在襁褓之中的時代,科學家們還找不到頭緒。
上世紀 80 年代,電視劇《霹靂遊俠》(Knight Rider)中的 KITT 自動駕駛汽車風靡一時。幾乎同時,汽車製造強國日本、德國和美國真正開始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發。日本的筑波工程研究實驗室、德國的慕尼黑國防軍大學與梅賽德斯聯合團隊、美國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分別以 “ 攝像頭為主、其他傳感器為輔 ” 開發出不同的自動駕駛汽車的原型,並且在真實路況中展現出了令人信服的能力。
尤其是卡內基梅隆大學的 NavLab ,在 1995 年完成了從匹茲堡到聖地亞哥的 “ No Hands ” 跨越美國之旅,其中 98.2 % 的里程由無人駕駛完成,雖然車輛速度不快,但即使放到今天來說,這樣的成果仍然非常了不起。這輛後來進入 “ 機器人名人堂 ” 的無人車是基於 Pontiac Trans Sport Minivan(小型多用途車)改造的,主要原因是相比轎車,Minivan 能塞進去更多的設備。後來 Waymo 也是採用了菲亞特克萊斯勒的 Minivan “ 大捷龍(Pacifica)” 作為無人車的改裝基礎。
90 年代末的另一個創舉來自意大利帕爾馬大學視覺實驗室 VisLab ,他們利用雙目攝像頭組成的立體視覺系統,在高速公路上實現了 2000 公里的長距離試驗,無人駕駛佔比 94 % ,而車速則達到了 112 公里/小時。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學術和產業界也開始了智能駕駛的探索。在清華大學,1978 年齊國光教授課題組開始研究自動駕駛,1986 年何克忠教授的 HTMR 課題組接力,到 HTMR-III,才真正有了接近自動駕駛汽車的原型車。
中國第一輛自動駕駛汽車是 90 年代初的 ATB-1(Autonomous Test Bed-1),由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五家單位聯合研究,而後的 ATB-2 速度較之第一代提升了 3 – 4 倍,這些院校多數成為了後來中國無人駕駛人才的搖籃。
同樣是 90 年代,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王飛躍教授在美國也開始了無人車的研究。
與美國類似,中國在遙控駕駛方面的探索也較早,1980 年國家立項“遙控駕駛的防核化偵察車”項目,哈爾濱工業大學、瀋陽自動化研究所和國防科技大學參與了該項目的研究。在第二個階段來臨的前一年( 2003 年),國防科技大學與一汽合作的紅旗 CA7460 實現了高速公路的自動駕駛演示,峰值速度達到 170 公里/小時,並且實現了自動超車。
2004 年~2009 年——第一個 6 年:孕育
2004 年的大事件是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無人車挑戰賽 “ Grand Challenge ” 。時值 “ 第二次海灣戰爭 ” 剛剛開始,國防部注意到沙漠行動中的士兵傷亡,希望用無人駕駛來解決這一問題。
DARPA 挑戰賽是美國的一項優良傳統,國會撥專款,通過挑戰賽發現那些變革性的、高回報的科研成果,極大地縮短了基礎科學發現與軍事應用之間的鴻溝。3 次無人車挑戰賽、1 次機器人挑戰賽(Robotics Challenge),以及 2018 年的航天發射挑戰賽(Launch Challenge),使其天下聞名。
挑戰賽要求無人車成功穿過240公里的沙漠道路,不出意料,2004 年所有車隊在沙漠中折戟。這讓隨後 2005 年的挑戰賽成就了一段光輝歲月。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 Red 車隊是奪冠熱門,其負責人、機器人專家雷德·惠塔克(Red Whittaker)志在必得。他認為無人駕駛不是僅僅靠努力工作就能實現的,“ If you haven’t done everything, you haven’t done a thing. ”意思是你什麼都得會,才能夠取得成功,只懂某些方面等於零。這也間接道出了無人駕駛的高門檻。
在參賽隊伍中,斯坦福大學的 “ 斯坦利(Stanley)” 無人車並不起眼,可是領隊塞巴斯蒂安·特龍(Sebastian Thrun)矢志奪魁,他是機器人 SLAM(同步定位與地圖創建)技術的先驅者,先前從卡內基梅隆大學失意出走,試圖在這場比賽中奪回尊嚴。無人駕駛車的傳統三強是卡內基梅隆大學、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但在挑戰者當中還有一個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年輕人,安東尼·萊萬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這個身高 2L米、特立獨行的年輕人以一輛名為 “惡靈騎士” 的摩托車參賽,吸足了眼球。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兩輛車一路領先,可下半程莫名的故障導致兩輛車大幅減速,只獲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斯坦利 ” 雖然在比賽中出了幾次事故,但沒有大礙,在刪除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代碼後竟然越跑越快,最終斬獲 200 萬美元的冠軍獎金。一直到 12 年以後,卡內基梅隆失利的原因才浮出水面,原來是引擎控制模塊和噴嘴之間的一個過濾器壞了,使引擎失去了動力。“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對待無人駕駛要有十二分的敬畏之心。特龍後來感嘆,斯坦福能贏,純粹是隨機性發生作用。
在這次比賽中,很多車輛都使用了激光雷達、高精度的地理信息系統和慣性導航系統,直到今天這些仍然是很多無人車的標準配置。當然,那個時候的激光雷達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其中霍爾(Hall)兄弟做的激光雷達大如臉盆,這兩兄弟是音響店的老闆,又是 “ 格鬥機器人 ” 的愛好者,從鑽研機器人到研究激光雷達,成就了後來激光雷達領域的先鋒 —— Velodyne。

筆者第一次接觸無人車就是在 2005 年,當時英特爾研究院的 Gary Bradski(OpenCV 之父)幫助特龍的團隊提升視覺能力,他力勸英特爾的市場部門贊助斯坦福車隊,彼時英特爾已經花了 10 萬美元贊助卡內基梅隆大學,於是特龍給了個友情價—— 2 萬美元,英特爾幸運地贏得了這個最終冠軍的賭注。有趣的是,由於“斯坦利”全身已經貼滿各種贊助商的商標,英特爾的標誌只能貼在前車窗上,這是個很醒目的位置,而且昭示這是輛無人車(因為沒有司機透過前車窗看後視鏡)。
轉眼到了 2007 年,DARPA 已經不滿足於荒野的無人駕駛,開始 “ 城市挑戰賽 (Urban Challenge)”。卡內基梅隆大學捲土重來,這次他們準備充分,組建了一支 40 人的隊伍,其中包括大將克里斯·烏爾姆森(Chris Urmson)。除了兩輛參賽的車輛,還有一輛補給車提供充足的零件替換。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惠塔克終於摘得桂冠。據說,這次卡內基梅隆大學投入巨大,以至於拿到 200 萬美元大獎後依然沒有填補虧空。在他們的裝備庫里,第一次出現了一種新型的 64 線激光雷達,為了讓這件裝備投入使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工程師編寫了大量的驅動程序。霍爾兄弟的 Velodyne 提供了這一超級武器,從臉盆大小到花盆大小,凝聚了他們的很多心血。在其後的近 10 年間,64 線激光雷達成為全世界絕大多數無人車必須配置的組件。
兩次挑戰賽極大地振奮了科研屆的信心,也培養了大量人才。據說谷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是個極客,他與特龍因為對機器人感興趣而成為密友,對於無人駕駛,佩奇有了新的想法。他把特龍招來谷歌,先是在谷歌街景上小試牛刀,到 2009 年的時候,秘密成立了無人車項目 “司機(Chauffeur)”,並且聚集了一批在挑戰賽中聲名鵲起的名將,包括前面提到的烏爾姆森和萊萬多斯基。
阿姆儂·沙書亞(Amnon Shashua)是一位視覺專家,屬於麻省理工派,在斯坦福學術休假時是特龍的室友。作為希伯來大學教授,他創建了 Mobileye,是第一個試圖產品化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技術的先驅者。Mobileye 創建於 1999 年,到 2009 年時,走過了 “ 從 0 到 1 ”的苦旅,已經有多款車型安裝了它的產品。創立之初,沒有人想到它一直到 2014 年才敲鐘上市,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2017 年它被英特爾收購,而這 18 年,它走出了一條少有人走的道路。
DARPA 的無人車挑戰賽激勵了中國的同行。2009 年,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 視聽覺信息的認知計算 ” 重大研究計劃的支持下,首屆中國 “ 智能車未來挑戰 ” 大賽在西安舉行,從此拉開了中國系列挑戰賽的序幕。
2010 年~2015 年——第二個6年:成長
2010 年,特龍以創始人身份成立Google X,在這裡,無數 “ 登(Moonshot)” 項目爭先恐後地展開。
項目必須符合 3 個條件:
- 惠及億萬用戶
- 看上去有點科幻
- 用今天的技術幾年內可以實現
毫無疑問,無人駕駛符合這些條件。
谷歌的第一款無人車是基於混電車 Prius 改裝的,頂上裝着 64 線激光雷達,以此建立高分辨率的三維環境模型或高精度地圖。這些測試車被偽裝成街景的數據採集車,常常夜間出沒,以躲避公眾的視線,也可以在沒人沒車的道路上採集高精地圖。即使他們非常低調,但也難免被交警抓到,詹姆斯·庫夫納(James Kuffner)是最早一批從卡內基梅隆車隊被挖到谷歌的工程師之一,如今已經是豐田無人車領袖的他,還能回想起當初被交警攔下的一幕。“ 紙包不住火 ”,最終著名記者約翰·馬爾科夫從某個測試司機的高中同學那裡挖掘到驚天信息,並且在《紐約時報》將其揭露出來,這讓 “車城” 底特律陷入深深的震驚之中。旋即內華達成為了美國第一個允許無人車上路的州。
谷歌無人車的核心骨幹中,有當初 “ 惡靈騎士 ” 的主人萊萬多斯基。這位深受佩奇賞識的年輕人,卻是個藐視規則,甚至對安全不以為然的麻煩製造者。他主導谷歌向 510 SYSTEMS 等幾家公司採購技術和部件,後來大家才知道這些公司是萊萬多斯基自己私自經營的。佩奇對其展現出極大的容忍,不僅許以重金,甚至把 510 SYSTEMS 買了下來。
谷歌的第二代無人車是更為強大的 Lexus ,同樣是混合動力。前面提到,無人車的基礎車型,第一個要求是要大,裝得下各種設備,第二個要求就是電控,因為發動機的底層控制算法比電機要困難很多,多數團隊更願意把時間放在高層的算法上。
但真正讓世人側目的是 2014 年穀歌第三代無人車 “螢火蟲(Firefly)”的誕生,這款長得像考拉的小車是針對無人駕駛完全進行重新設計的,比如移除了雨刷,因為並不需要有駕駛員在雨中看清路況。按照設計,這種車是沒有方向盤的,但由於加州法律的限制,車裡還是安裝了一個遊戲操縱桿作為方向盤。這輛車後來獲得了紅點設計大獎。
與此同時,Mobileye 贏得了車廠的信任,以視覺為主的 ADAS 低價方案進入主流市場,到 2015 年時,裝機量已經近千萬台。Mobileye 也偷偷開始了自動駕駛的研發。相比谷歌的方案,Mobileye 基於視覺的方案有獨到之處。比如它採用視覺地圖,從視覺中提取的地圖特別小(每公里只需10 kb 級別的數據,相比之下谷歌是 GB 級別的),適合實時上傳、通過眾包的方式更新。事實上,基於視覺的定位更接近於人類的駕駛方式。我們根據道路上的標誌來評估大致的位置,並且根據路麵線條的變化做出實時的決策(選哪一條車道,是否上匝道等)。那麼,只需從視覺中提取出那些標誌和線條,眾包上傳到地圖,行駛時便可以通過視覺匹配來獲得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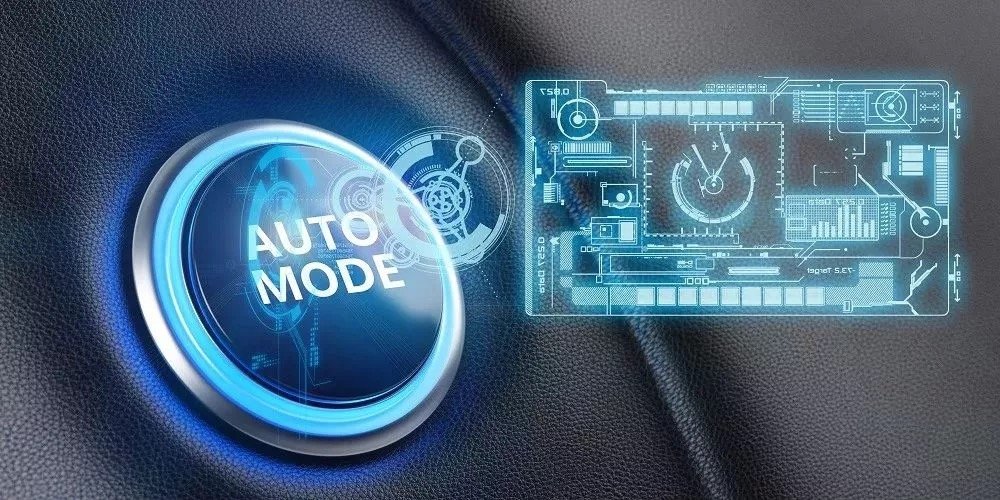
實際上,2015 年還發生了幾件大事。
首先是年初,梅賽德斯-奔馳的無人駕駛概念車 F015在 CES 上驚艷亮相,一下子把無人車呈現到大眾面前。
2 月初,新聞爆出打車應用 Uber 從卡內基梅隆大學及其附屬的國家機器人研究中心挖走 50 多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建立自己的無人車研發團隊。據說Uber的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乘坐了谷歌的無人車(谷歌是 Uber 的投資人)之後,既興奮又恐懼,認為這對於行業來說是顛覆性的技術,然而又會 “ 革掉自己的命 ” ,於是有了前面的大動作。
而最讓人直面 “ 未來已來 ” 的,是 10 月份特斯拉發布 Autopilot。雖然 Autopilot 是 L2 級的輔助駕駛,但很多普通車主都被這個名稱給誤導了。三個膽子比較大的司機打開 Autopilot 模式,完成了美國東西海岸的穿越,全程平均速度達到了 84 公里/小時。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險情,而特斯拉卻不以為然,從而為後來的事故埋下了隱患。
2010 年 — 2015 年的這個階段,中國略顯沉寂。
2010 年,前面提到的 VisLab 四輛自動駕駛汽車從意大利帕爾馬出發,穿越 9 個國家、行程 1.3 萬公里,到達中國上海。VisLab與中國的淵源並未結束,後來國內一些無人駕駛的青年軍在 VisLab 做過訪問學習。2015 年,一家華人背景的視覺芯片公司——安霸收購了 VisLab 。
2011 年 7 月,國防科技大學賀漢根教授技術團隊自主研製的紅旗 HQ3 無人駕駛汽車,首次完成了從長沙到武漢 286 公里的高速全程無人駕駛試驗,其中人工駕駛里程不足 1 %,而且相比上一代的 CA7460,在硬件小型化、控制精度和穩定性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基於此,國防科技大學也拿到了當年“智能車未來挑戰”大賽的冠軍。而這之後,李德毅院士的團隊成為冠軍的常客(除了 2013 年由北京理工大學獲得,其主將是馭勢科技 CTO 姜岩博士)。
而在 2015 年的下半年,有三個值得回憶的事件。
- 8 月份,宇通和李德毅院士團隊合作的大巴完成了鄭開高速的 33 公里無人駕駛,在世界範圍內開創了無人駕駛大巴的先河。
- 11 月第 7 屆 “ 智能車未來挑戰 ” 大賽在常熟成功舉辦,挑戰賽得到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報道,無人駕駛成為了普通大眾飯後茶餘的談資。
- 12 月份百度推出無人車年度大片,百度與寶馬合作的無人車在 G7 “ 高速-五環-奧林匹克森林公園 ” 的路線中進行了往返行駛,吸引了無數眼球。對於這個項目中的一些人來說,這次演示是一個結束,隨後他們離開百度開始新的征程。而對百度來說,這是一個開始,自動駕駛部門正式成立,王勁挂帥,號稱 “ 三年商用,五年量產 ”、“ 如果汽車行業不革自己的命,就會被別人革了命 ”。
這三個事件讓國人意識到,在無人駕駛這個高精尖領域,中國並沒有缺位。
2015 年,已是爆發的前夜。
2016 年~2021 年 ——第三個 6 年:開花
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道:
“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用這段話描述 2016 年的開局,再恰當不過。2016 年是無人駕駛的 “ 春分 ” 時節。
筆者於 2016 年 2 月辭職創業,很多人,包括風險投資(VC),對商業模式滿腹狐疑。孰料 3 月份連爆幾件大事,AlphaGo 五番棋大勝李世石點燃了民眾對人工智能的熱情,而通用汽車以 10 億美元收購彼時只有幾台樣車、40 多個人的 Cruise Automation,讓 VC 也意識到,無人駕駛時代即將來臨。在中國,北京的春季車展,長安與博世和清華合作的幾輛無人車 “ 2000 公里進京 ” ,無人駕駛也真正進入中國大眾視野。
4 月份峰迴路轉,英特爾高調宣稱押注智能駕駛領域,筆者作為英特爾老員工、又在做無人駕駛創業,對此也非常關注。5 月份英特爾聘請的諮詢公司找到筆者,期望為英特爾的策略建言獻策,我的建議很簡單,收購Mobileye。1 年以後,英特爾宣布以 153 億美元收購 Mobileye(與本人的建議未必有因果關係),代表了這個 PC 時代的巨頭正式大舉進入這一領域。
春寒料峭,幾起事故讓人陡生疑慮。
- 2 月份谷歌的無人車撞上了巴士,這是其第一起主動承認有責任的事故,但那起輕微碰撞並未引起太多指責,後面總結出來的教訓之一是巴士司機惹不起。
- 5 月份,特斯拉的第一起致命車禍佔據了頭條。死者是一位司機,特斯拉的熱衷者。當時車輛運行在高速 Autopilot 模式中,司機卻在觀看視頻,完全忽略了緊盯路況的責任。Autopilot 系統沒有檢測到一輛大卡車正橫穿馬路,車輛以極高的速度從卡車肚子下鑽了過去,司機當場身亡。
事故中縱然有 Mobileye 視覺未能識別出白色拖車橫側面的緣故,但前視雷達也由於安裝位置較低錯過了目標。公眾開始質疑:這類 beta 版的軟硬件是否允許上路?軟件升級了是否要重新車檢?另一方面,Autopilot 被錯誤宣傳成了自動駕駛,而實質上仍然是輔助駕駛。
1 個月後,在媒體和業界的口誅筆伐中,特斯拉發了一篇博客給自己辯解,事故前的 7 個月中 Autopilot 完成了 1.3 億英里的自動駕駛里程,而美國人類駕駛員平均每 9400 萬英里發生一次致命車禍,Autopilot 豈不是已經足夠安全?然而,特斯拉沒有把中國此前的一次類似車禍算上,因為那樣的話,Autopilot 的數據降成了每 6500 萬英里發生一次致命車禍。此後關於多少無事故里程才算安全,也成為擺在行業面前的無解之問。
這起事故也導致了特斯拉與 Mobileye 的 “ 分手 ” ,除了事故表面的責任,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特斯拉想要自主研發計算機視覺的雄心觸碰了 Mobileye 的核心利益。在幾個回合的相互指責後,特斯拉先是宣布把博世的毫米波雷達作為主傳感器,到 10 月份,它正式宣布 Autopilot 硬件版本 2.0(HW2)採用自己的視覺系統。也許是馬斯克的 “ 第一性原理 ” (人靠視覺能夠駕駛,無人駕駛也一樣),也許是特斯拉的促銷手段,他們宣稱,HW2 具備了全自動駕駛的能力,購買 HW2 的新車,只需花 3000 美元,未來便能夠通過軟件升級實現無人駕駛。略顯諷刺的是,恰恰 2 年之後,2018 年 10 月,特斯拉從宣傳冊里刪掉了這個選項。這兩年中,特斯拉經歷了大量人才的流失,多個測評顯示,HW2.x 在推出 1 年以後才基本達到 1.0 的水準。但是對 2.x 軟硬件的完全控制還是讓特斯拉掌握了大量的數據。
2016 年 8 月的一件大事是Uber耗資 6.8 億美元收購卡車自動駕駛公司 Otto。當初卡蘭尼克在匹茲堡成立研發中心時,對於無人駕駛進入商業化有着極高的期待,然而 1 年多的進展並不令其滿意,收購 Otto 是再次加碼,可是他沒有想到,這日後成為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Otto 的創始人正是當初那位任職於谷歌、桀驁不馴的萊萬多斯基。佩奇的包容沒有讓他收心,谷歌巨額獎金帶來的滿足感也漸漸消退,大公司的繁文縟節和小心翼翼讓他深感 “ 龍困淺灘 ”,於是在 2016 年年初,他拉了一幫人出來另立門戶。硅谷對 “背叛” 相當寬容,但鑒於無人駕駛這種技術的稀缺性,谷歌有可能與出走者簽署某種非正式的競業條款,出走者在創立新公司時多數刻意避開了直接競爭。比如朱家俊和 Dave Ferguson 的Nuro 做物流配送,而 Otto 則定位做無人駕駛的卡車。當然,任何條款都有限期,收購發生的 8 月,恰好是萊萬多斯基拿到谷歌最後一筆補償金之後。
谷歌已經意識到無人駕駛人才的流失,改變組織和激勵機制迫在眉睫。
2016 年 12 月,Waymo 作為一家獨立的公司從 Alphabet 母體中拆分,一夜之間這個全新的名字成為無人駕駛領域舉世矚目的第一高手。在此之前 3 個月,約翰·克拉夫西克(John Krafcik)成為這支團隊的新首領,這位既做過汽車公司老總(前現代汽車北美 CEO),又領導過互聯網公司(類似二手車交易網站)的老兵,給 Waymo 帶來了不同的風格和戰略的同時,也必然帶來了衝突。在克拉夫西克入職前1月,特龍之後的第二代領袖烏爾姆森也離職創業,Waymo 真正進入了新的時代。
如果 2016 年是 “ 春分 ”,2017 年則是 “ 雨水 ” 。
雨水充沛,萬物復蘇,很多公司大踏步而來。大公司,無論是科技巨頭還是主機廠,開始真正投入資源。同時,2017 年是創業公司紛紛入局的一年。另一個重要的跡象是,無人駕駛百花齊放,不僅僅是乘用車,還出現了各種商用車、專用車,除了載人之外,物流變成一個更大的市場。

1 月份的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CES)是個風向標。這一年的最熱話題是自動駕駛,LVCC 北館幾乎每家公司都展出了自動駕駛概念,北廣場則是自動駕駛的實車體驗。筆者所在的馭勢科技也向世界推出了概念車 “ 城市移動空間 ”,其具有 360 度無死角傳感器覆蓋和沒有方向盤油門剎車的 L4 級自動駕駛設計,特別是獨特的內部環形沙發布局彰顯了“在路上的 VIP 休息室”概念。很多老牌車廠高管、工程師和設計師在車前駐足,其中一位慨嘆,在主機廠早就想這麼做,可惜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時代周刊》(Time)的汽車門戶特邀主編 Alex Roy 在播客上說:“當我看着這輛車時,我認為這是 Faraday 本應該去造的車。” 該車在2017年獲得了紅點設計大獎,在紅點的歷史上,還有三輛無人車獲獎,前面提到的谷歌 “ 螢火蟲 ” 、奔馳 F015 和同年的寶馬 i-inside。
4 月份,英特爾以 153 億美元收購 Mobileye ,這個動作姍姍來遲,在過去的1年中英特爾全力奔跑,但CEO 柯再奇(Brian Krzanich)已沒有耐心從頭追趕,收購Mobileye是獲得前排車票的最佳選擇。153 億美元,按照傳統的財務指標來說這個價格是高的,按照 ADAS 公司的估值來說也一定是高的,但如果以自動駕駛龍頭的想象空間來看,似乎也不高。僅僅 2 個月後,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師給了 Waymo 一個 700 億美元的估值。
英特爾與 Mobileye 的整合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涉及美國與以色列、新舊勢力的平衡,但 “ 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虹 ” ,18 年後重裝再發時,英特爾已經成為這個競技場最重要的玩家。
不同文化的整合需要領導的魄力和妥協,需要信任和授權。在過去的 1 年裡, 通用汽車也是潛流暗涌,Cruise 的 L4 級無人駕駛新生力量與 SuperCruise 的 2 級自動駕駛產品團隊該如何相處?瑪麗·巴拉(Mary Barra)領導的管理層運用了最高的政治智慧,底特律的歸底特律,舊金山的歸舊金山,Cruise 團隊獲得了極高的自主權,在人員快速發展的同時,力圖保留硅谷的創業文化;另一方面,通用汽車又提供了硅谷所不具備的汽車工程能力,兩者取長補短,使 Cruise 很快在舊金山繁忙的街頭展示了高超的水平,成為 Waymo 之後進步最快的追趕者。對於 Cruise 來說,舊金山是顯示實力的最佳主場,它聲稱,比起 Waymo 和 Uber 在亞利桑那的那幾個城市(當然 Waymo 並不只是在亞利桑那),舊金山複雜度提升了數十倍。
美國汽車市場的 “ 二當家 ” 福特也不甘落後。福特從來沒有忘記昔日榮耀(家族人員依然身居高位),它也是最早開始與谷歌接觸的汽車公司,然而互聯網公司的傲慢使談判不歡而散。2016 年,福特推出 2021 自動駕駛宣言 —— 在 2021 年實現無人駕駛的商業化運營。2017 年年初,又有以 10 億美元投資Argo AI 這樣的大手筆。Argo AI,這家剛剛成立數月的創業公司擁有谷歌、Uber 和早年參與挑戰賽的一些高手。
然而,對於老牌巨頭們來說,新舊動能的轉換是掙扎的,新業務需要長期和巨量的投入,而舊業務一旦陷入成長困境,領袖將承擔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福特老 CEO 馬克·菲爾茲(Mark Fields)黯然退位,但還是把權杖交給了負責自動駕駛和出行部門的負責人——吉姆·哈克特(Jim Hackett)。哈克特上任後給 “ 2021 ” 降了點溫,但這可以被理解為 “ 管理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值 ”,對於團隊來說,“ 2021 ” 仍然是值得努力的目標,福特和 Argo AI 的目標先鎖定在邁阿密。與通用選擇的舊金山相比,邁阿密交通狀況更為複雜,需要應付很多遊客,雨水更多,甚至經常 “ 水漫金山 ”。
還有很多老牌巨頭也在應對新舊動能轉化的陣痛。零部件供應商采埃孚 ZF 在一系列投資和收購之後(對激光雷達供應商 Ibeo 的成功收購形成了對競爭對手Valeo的狙擊),也經歷了領導層的巨變。在汽車圈裡,“ 分 ” 與 “ 合 ” 蔚然成風。“ 分 ” 可以輕裝上陣迎接新四化(新能源化、共享化、智能化、網聯化),能夠更快決策,更容易融資。
典型的案例就是德爾福拆分出安波福,全力聚焦智能網聯汽車(幾乎與此同時,又以 4.5 億美元併購了初創公司NuTonomy)。福特也拆出Ford Autonomous Vehicles LLC。另一方面,通過 “ 合 ” 化敵為友,抱團取暖,分擔研發成本,也不失為上策。
於是,在這個競技場里,大家各自站隊,迅速形成不同的聯盟。比如,
- 英特爾 / Mobileye、安波福、寶馬一個圈子,後來又加入了大陸、菲亞特克萊斯勒等。
- 英偉達、博世、ZF、大眾/奧迪、沃爾沃等又是一個圈子。
- 出行服務商Uber有戴姆勒、沃爾沃、豐田的朋友圈,
- 而 “ 老二 ” Lyft 也有通用汽車、安波福、捷豹路虎等夥伴。
單以聯盟成員的規模來說,百度阿波羅生態可以說是最大的朋友圈:2017 年 3 月,陸奇入主智能駕駛事業部,引起了另一撥核心人才的出走。據說,此時百度美國研究院一位工程師建言開源,百度領導層迅速展現了巨大的魄力,在 4 月份的上海車展上,陸奇宣布 “ 阿波羅 ” 計劃,做汽車界的安卓。
阿波羅登月計劃,寓意是向人工智能的宇宙出發,“ 希望未來可以解放雙手,使每個人開車時也能自由地仰望星空。”
一石激起千層浪,整個行業為之震動。在 7 月份的 AI 開發者大會上,李彥宏乘坐一輛與博世合作的蘇州牌照汽車,在五環展示了一番自動駕駛技術,接到交警罰單,但這不能掩蓋 Apollo 1.0 的宣布所引起的轟動,大家開始意識到,百度是認真的。
阿波羅的開放,值得全行業豎大拇指,在活躍生態、數據共享、培養人才等方面居功至偉。但也引發了很多問題:
- 安卓的成功是在一個成功的 iOS 之後,目前尚無成功的無人駕駛 iOS,做安卓是否過早?
- 安卓是谷歌聲東擊西的秒策,因為安卓是移動端提升其核心搜索和廣告業務的載體,而阿波羅自身的商業模式還沒有浮現,與今天百度的核心業務也尚未有機結合,作為一個 “ 燒錢 ” 的業務是否能夠得到股東的支持、長期走下去?
- 阿波羅生態的繁榮,不在於百度的慷慨,而在於生態成員是否也能全情投入,尤其是那些汽車產業的 “ 老炮 ” ,是否認同 “ 以數據換代碼 ” 的這條路徑?
- 阿波羅的開源,對初創公司是禍是福?尤其是那些百度系的初創公司?
毫無疑問,對於初創公司來說,阿波羅降低了做演示的門檻,但同時也提升了做大做強的門檻,必須做到比阿波羅的技術有差異化提升才能生存下來。很多創業公司的差異化是垂直化、場景化和加快商業化落地,從卡車物流到末端配送,從載人、載物到載功能(比如環衛清潔),從礦山到港口,從園區到機場和最後 1 公里。
在 2017 年,值得一提的商業化落地事件有三個。
- 第一,4 月份馭勢科技與白雲機場在航站樓與停車場之間的擺渡,是國內第一起公開的無人駕駛運營,雖然僅僅一周,但與演示有本質的區別,如果說演示是規定時間、規定路線,運營則是面向終端用戶和開放環境、全時態工作。
- 第二,6 月份馭勢科技與凱德集團在杭州來福士地下停車場的擺渡服務,是國內第一起長達數月的多輛無人車常態化運營,開放的人車環境、狹窄的車道、沒有 GPS 的定位,都是技術亮點。
- 第三個事件是年底深圳的阿爾法巴,4輛經過改造的大巴在設計好的公交路線上展示了不錯的能力,這是創業公司和高校合作的結果。讓人始料不及的是大量 “ 震驚體 ” 文章的刷屏,這與幾十年前羅森在Shakey 上碰到的問題如出一轍,在技術還在演進的過程中,管理媒體和大眾的預期至關重要。
當然,2017 年最有意義的事件發生在美國。
10 月中旬,Waymo 宣布,沒有前排安全司機的自動駕駛汽車已經開始上路試運營。
對於一家非常重視安全的大公司來說,這需要巨大的勇氣,以及對技術絕對的信心。當然,為確保安全,Waymo 仍有安全員在后座以備不測。2018 年年初,加州的車輛管理局進一步宣布 “ 允許車內不坐安全員、只需遠程安全員 ” 這個巨大的跨越,相信與 Waymo 所帶來的信心有關。
美國對無人駕駛的態度上,從奧巴馬到特朗普政府,從參議院到眾議院,從聯邦到州政府,具有極高的共識——美國要成為領導者。
兩任交通部長安東尼·福克斯(Anthony Foxx)和趙小蘭連續推動《自動駕駛汽車聯邦政策》、《自動駕駛系統 2.0:安全願景》和《準備迎接未來交通:自動駕駛汽車3.0》,在法律空間里增加豁免,為行業鬆綁。
幾乎同時,德國也推出了首部與自動駕駛汽車相關的法律——《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允許自動駕駛系統在特定條件下代替人類駕駛,同時全球第一部自動駕駛道德準則也應運而生。這些立法活動為世界第一款 L3 級自動駕駛產品——奧迪 2018 年款A8 的擁堵巡航(Traffic Jam Pilot)掃清了障礙。
中國也一直在探索無人駕駛立法和測試體系的建立。早在 2016 年,國家層面就開始討論路測規範,然而第一個宣布的是北京市,2017 年 12 月,北京市交通委聯合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等部門,制定發布了《北京市關於加快推進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有關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和《北京市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管理實施細則(試行)》兩個文件,如同平地一聲雷,讓年底的產業界振奮不已。既然第一塊牌已經落地,多米諾骨牌就不會停止。2018 年的上半年,上海、重慶、深圳、廣州等地紛紛推出當地的路測政策和指南。4 月 11 日,工信部、公安部和交通運輸部聯合推出《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管理規範(試行)》,在國家層面一錘定音。
考慮到中國的複雜路況對安全有更高的要求,國內的路測規範都要求測試主體事先在封閉測試場內進行一定里程的測試。早在 2016 年 6 月,由工信部批准的國內首個 “國家智能網聯汽車(上海)試點示範區” 封閉測試區在嘉定開園。隨後,形成了 “ 5+2 ” 的全國布局。時至今日,各地仍在修建或改造智能網聯汽車的測試場,雖然短期內有重複建設的問題,但從長期來看,未來,無人車無論是上市還是年檢,都有很大的需求。
2017 年的 “ 雨水 ” 過後,2018 年或許是 “ 驚蟄 ” ,既有商業化的隆隆春雷,也可能有倒春寒。
2018 年的開始讓一些人快樂,一些人難過。Velodyne 降價了,而且降了一半。2017 年對很多無人駕駛公司來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買不到激光雷達,要等好幾個月,當年底終於買到了,並囤了一部分貨時,結果市場上的激光雷達已經降價了。
這個時候,激光雷達的賽場已經不是 Velodyne 一枝獨秀了,Valeo 的 Scala 在奧迪 A8 上實現了第一個量產項目,傳統主機廠和供應商巨頭紛紛投資併購,僅德爾福(安波福)就押寶 3 家。幾乎所有公司都押注固態或半固態激光雷達,除了前兩年已經很火的 Quanergy 和 Innoviz,一些新創公司(如Luminar、速騰聚創和 Innovusion)也展現了性能更佳的產品原型。兩年前風光無兩的 Quanergy 在量產上碰到了一些麻煩,雖然它在光學相控陣技術這條路線上仍然領先,但基於 MEMS 微振鏡、光學二維振鏡和 Flash 技術的固態激光雷達在產業化上顯示了更快的進展,Innoviz 得到了寶馬的訂單,Velodyne 的新品 velarray 也似乎後發先至。
在剛剛過去的 2017 年,加州機動車輛管理局(DMV)公開的數據顯示,基於 35 萬英里的測試里程基數,Waymo 實現了每 5596 英里進行一次人工干預,緊隨其後的是 Cruise,每 1254 英里進行一次人工干預。相比 2016 年的每 5000 英里進行一次干預,Waymo 在 2017 年只提升了 10% ,讓人略感失望。細看 Waymo 的數據,積極的因素是,2017 年最後幾個月的每次干預里程數得到了極大的提高,2018 年是否延續這種趨勢,結果即將揭曉。
Waymo 的工程總監在麻省理工學院講座時,說了一句很深刻的話:
“When you are 90% done, you still have 90% to go(當你認為完成90%時,實際只走了10%)”
對於這一道路的艱巨性和長期性,Waymo 深有體會。然而,這家公司又很擅長 “訥言敏行”。Waymo 的 “ Early Rider 項目” 又向前邁了一大步。進入 2018 年,Waymo 在亞利桑那州的部分車輛中撤掉了安全員,早期乘客開始真正 “獨享” 無人車的空間。
2018 年 3 月,Waymo 與捷豹路虎簽署協議,請後者定製 2 萬台無人車。Waymo 的高歌猛進,給 Cruise 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此時通用汽車做出了一個巨大的決定,將 Cruise 推向資本市場,利用外部資本和資源來加速發展。5 月 31 日,軟銀宣布將向 Cruise 投資 22.5 億美元。僅僅一天之後,Waymo 就給出了回應——將購買菲亞特克萊斯勒的車輛數目提升到 6.2 萬台。8 月份,摩根斯坦利將 Waymo 的估值推到 1750 億美元,其中機器人自駕出租車業務估值 800 億美元,自動化物流服務估值高達 900 億美元。10 月 3 日,本田向 Cruise 進一步注資 27.5 億美元,也將 Cruise 的估值推到了 146 億美元。通用汽車以當初 10 億美元收下 Cruise,絕不曾想過兩年半後這一部分的估值已經達到通用汽車總市值的 1/3。聯想到英特爾以 153 億美元購買 Mobileye ,大可不必大驚小怪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雖然 2018 年一整年是資本的寒冬,但仍然不斷傳來無人駕駛公司融資的消息。無論是創業公司,還是風險投資(VC),都分裂成兩個陣營。
- 一個是硅谷范兒的 “火箭派”,其理論依據是既然無人駕駛是登月,那就擼起袖子造火箭。既然未來的大方向是出行,就一步到位做無人駕駛出租車的運營。有人評論這是“沒有 Waymo 的命,卻得了Waymo 的病”。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家公司像Waymo那樣土豪、一買就是 8.2 萬輛無人車,卻有兩位數的公司在商業模式上對標 Waymo,沒有 Waymo 的 “富爸爸”,只能長年靠 VC 買單。殊不知,即使是Waymo 的 8.2 萬輛車,獲得數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在 20、30 座道路乾乾淨淨的城市行駛,數據也不夠豐富和多樣化。這意味着,Waymo 的 L4 級商業化路徑存在可擴展性的問題。
- 另一個陣營是務實的路徑,從垂直細分做起,“農村包圍城市”。用賽車領域的話來說,想要第一個衝過終點線,你必須完成比賽,哪怕是從維修站出發。可是,在“火箭派”眼裡,這是“梯子派”,想登月,先造梯子,務實是務實,但未來的天花板太低。業界有不少 “diss” 這類路線的說法,Waymo 說我要飛、整天學跳怎麼行,有些 “高大上” 的基金認為,現在旱季你為了生存進化成了仙人掌,等雨季來了,你頂多只能是更高、更肥的仙人掌,已經長不成參天大樹了。固然這些說法有點偏頗,但確實有些垂直細分領域的場景,與開放道路 L4 級自動駕駛不搭,而且因為市場規模有限,無法獲得算法升華所需的大量數據。
看起來這兩條路徑都存在數據可獲得性的問題。那麼到底需要多少數據,或者通過多少里程來證明安全性呢?
就無人駕駛而言,Waymo 積累了最多的里程,2018 年 10 月時積累了 1000 萬英里。就算是加上 L2 級自動駕駛,我們前面說過,特斯拉在 2016 年的自辯,1.3 億英里、2 次人命事故,數據也是不夠的。美國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給出了一個數學模型,如果要在統計學意義上證明無人駕駛開得比人好 20%,需要 110 億英里。那就意味着,100 輛車,1 天 24 小時、1 年 365 天不停地跑,要跑 500 年。
特斯拉的一個啟示是:要學會靠用戶的車去獲得數據、驗證算法,如果有 1000 萬輛車,1 輛車只需跑1100 英里,110 億英里就達到了。
因此,一個更合理的路徑是,用火箭的技術造各種飛機,然後用飛機的錢和數據來提升火箭技術。具體而言,是用基於開放道路 L4 級的技術(火箭的技術),降維到具有確定邊界的 L3 級 / L4 級商業化場景(各種飛機),大規模部署這些場景,獲得現金流和大量數據後,進一步突破開放道路 L4 級的局限。馭勢科技採用了這樣的策略,在高速公路 L3 級、最後 3 公里微循環 L4 級、停車場自主泊車和機場無人物流拖車方面取得了商業化的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馭勢與上汽通用五菱實現了全球首次自主泊車的終端用戶交付,一鍵實現遠距離泊車、一鍵實現召車。類似的技術在與首汽 Gofun 合作的分時租賃中也開始使用,讓用戶實現自動取車和還車,同時運營方又可以通過場站間的無人編隊調度降低運營成本。這些場景的部署帶來了大量交通場景的數據,從而反哺開放道路 L4 級自動駕駛算法的進化。
2018 年的 “灰犀牛” 是事故。當整個行業進入深水區,事故已經成為大概率的風險。Waymo、Uber 和特斯拉都出現了多起事故,且後兩者都出現了致命的事故。
自從 Uber 收購 Otto 後,一些變化在悄然發生。萊萬多斯基對安全的藐視使公司文化發生了變異,在舊金山的 Uber 辦公室里有一條標語是 “安全第三”。路透社後來指出,Uber 的測試車改成沃爾沃 XC 90後,新的改裝設計擴大了傳感器的盲區,而高聳的 64 線激光雷達改變了車的重心結構,然而 2017 年的一次側翻並沒有引起太多重視。自萊萬多斯基離開 Uber,新 CEO 上任後對自動駕駛的態度開始模糊。
據 Business Insider 報道,團隊擔心項目取消,必須用快速進展取悅領導,又要迎合領導對平順性的要求,因此忽略了很多安全設計。這些因素積累下來,最終導致 3 月 18 日那起世界首例無人駕駛汽車引起的致命車禍事件(特斯拉的那幾次不算無人駕駛)的發生,一輛 Uber 無人車夜間行駛時撞死了一名推着自行車違章橫穿馬路的行人。固然有那位行人自己的責任,還有 Uber 安全駕駛員的重大責任(跟特斯拉的第一起致命事故類似,又是在看視頻),但 Uber 自身的諸多問題無從推脫,比如技術上為了平順性把原車的自動緊急剎車系統禁用,錯失了最後一秒的安全保障,而在管理上從車上 2 個人縮減到 1 個人。事故後 Uber 暫停了所有的測試,重新審視安全設計和管理,一直到年底才重新上路,教訓可謂慘痛。陰雲籠罩下的另一則新聞是 Uber 關閉了自動駕駛卡車部門,這使得當初對 Otto 的收購更加無一是處。
做無人駕駛,不可或缺的是對安全的敬畏之心,以及對行業基本規律的尊重。Waymo 也發生了幾起事故,包括一位安全員睡着導致的車禍。The Information 先後曝光 Cruise 和 Waymo 無人車在真實路況中依然不甚理想,路透社 10 月的一篇文章也指出 Cruise 達到 L4 級量產依然路途漫漫。在這個領域,輕言 L4 級量產、忽略安全大躍進式發展,必然付出代價。
Waymo 採取了 “進二退一” 的策略。10 月 30 日,加州車管所向 Waymo 頒發了完全無人駕駛測試牌照,即可以合法在加州公開道路上測試沒有安全員的無人車。然而 11 月底,經過深思熟慮,Waymo 重新又把安全員放回了駕駛座。同時,Waymo 任命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前主席貝博拉·赫斯曼(Deborah Hersman)為首席安全官。
12 月初,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郊區,名為 Waymo One 的無人駕駛出租車付費服務正式開始運營。在此之前,克拉夫西克照例大談了一下困難,認為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 L5 級自動駕駛還需要等幾十年,希望媒體和大眾降低對它的期望。
回到這句話 “When you are 90% done, you still have 90% to go(當你認為完成 90% 時,實際只走了 10%)”,如果今天的技術和成本要求無法快速解決最後 10% 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通過人-車-環境的整體思路去解決呢?這就是車路協同的概念。
2018 年,中國正孕育着全新的基礎設施,阿里和百度等都提出 “車路協同” 的概念,基於 LTE-V2X 和 5G 帶來的超視距感知能力和高可靠低延遲鏈路,可以把一部分感知和決策能力放在路端,利用邊緣雲的思路去解決環境和基礎設施的問題。
車端計算是價值鏈上另一個重要的元素,尤其是芯片。高級別無人駕駛採用的主芯片要麼來自英偉達,要麼來自英特爾/Mobileye。自從出現中興被封殺事件,美國又祭出商務管制清單,對於中國的業界來說,需要未雨綢繆。華為、寒武紀、地平線等國內芯片商正加速開發適用於無人駕駛的 AI 加速芯片。隨着無人駕駛算法逐漸固定下來,專用的加速芯片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特斯拉也採用了這個策略。
價值鏈上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是數據,無人車要想變得越來越聰明,需要數據。歐盟在數據立法上一向走在前面,《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號稱史上最嚴格,讓無數互聯網公司焦頭爛額,數據是資源、也是燙手山芋。對互聯網公司如此,但對車廠卻很寬容。歐盟最近一次關於自動駕駛車輛註冊的投票中,7A 條款確定 “自動駕駛汽車產生的數據是自動生成的,其本質不具有創造性,所以不適用於版權保護或數據庫權利”。這意味着,無需車主同意,車廠就可以收集自動駕駛汽車產生的數據(包括 GPS 軌跡信息在內的遙感信息),並可以將其出售給第三方。這可以說為車廠做了最佳助攻。

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要求重要數據不能出境,外資和合資車廠無法將數據送至國外去研發,因此在國內建立研發團隊和研發供應鏈勢在必行。這是國內科技公司和新晉供應鏈玩家的絕佳機會。
2018 年即將結束,距 2021 年還有 3 年,業界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確定區域(比如城市的一個區域)L4 級無人駕駛的規模化應用。從目前看,我們可以保持謹慎的樂觀。
2022 年~2027 年 ——第四個 6 年:結果
如果第 3 個 6 年的目標順利實現,第 4 個 6 年將是開放道路 4 級無人駕駛的大興之時。
無人駕駛帶來的變化遠遠不止是汽車產業,它將徹底改變出行和物流,改變這個世界原子的移動。
到第 5 個 6 年( 2028 年 – 2033 年)時,路上川流不息的車輛大多數將是無人駕駛共享汽車,汽車數量減少一半以上,但汽車的利用率得到極大提升,堵車將成為過去,天空重歸於藍,停車位被改成公園、活動空間和住所,車禍幾近於零。
交通流、信息流、能源流三流合一,所有與人或物相關的交通將被重新定義,保險業需要涅槃重生,而服務業將找到新的爆發點 ——上述的無人駕駛出租車是除了家和辦公室的第三空間,是移動的商業地產、移動的影院、移動的辦公空間、移動的咖啡館。
智能駕駛是人工智能與傳統汽車相結合的創新產物,是汽車行業發展的未來。作為一項變革性的技術,智能駕駛既是技術創新又是社會創新,無論是法律、法規和政策,還是道德倫理爭論,我們都要有勇氣和耐心,呵護和引導其健康發展。
熱切期待道路不堵、天空很藍、自由出行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本文出自賽迪研究院主辦的《人工智能》雜誌 2018 年 12 月刊,作者為吳甘沙、張玉新。原標題:《智能駕駛進化史:夢想照進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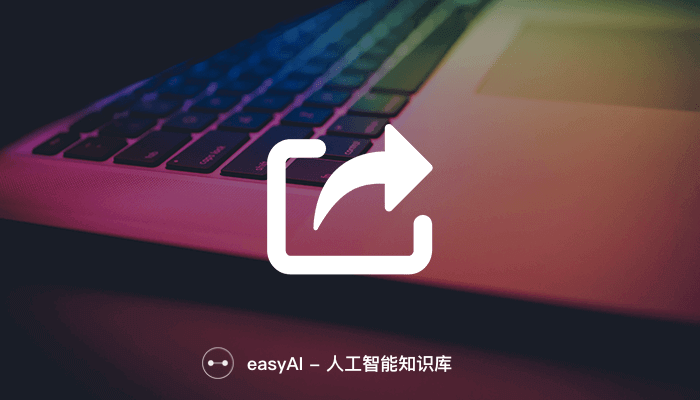

Comments